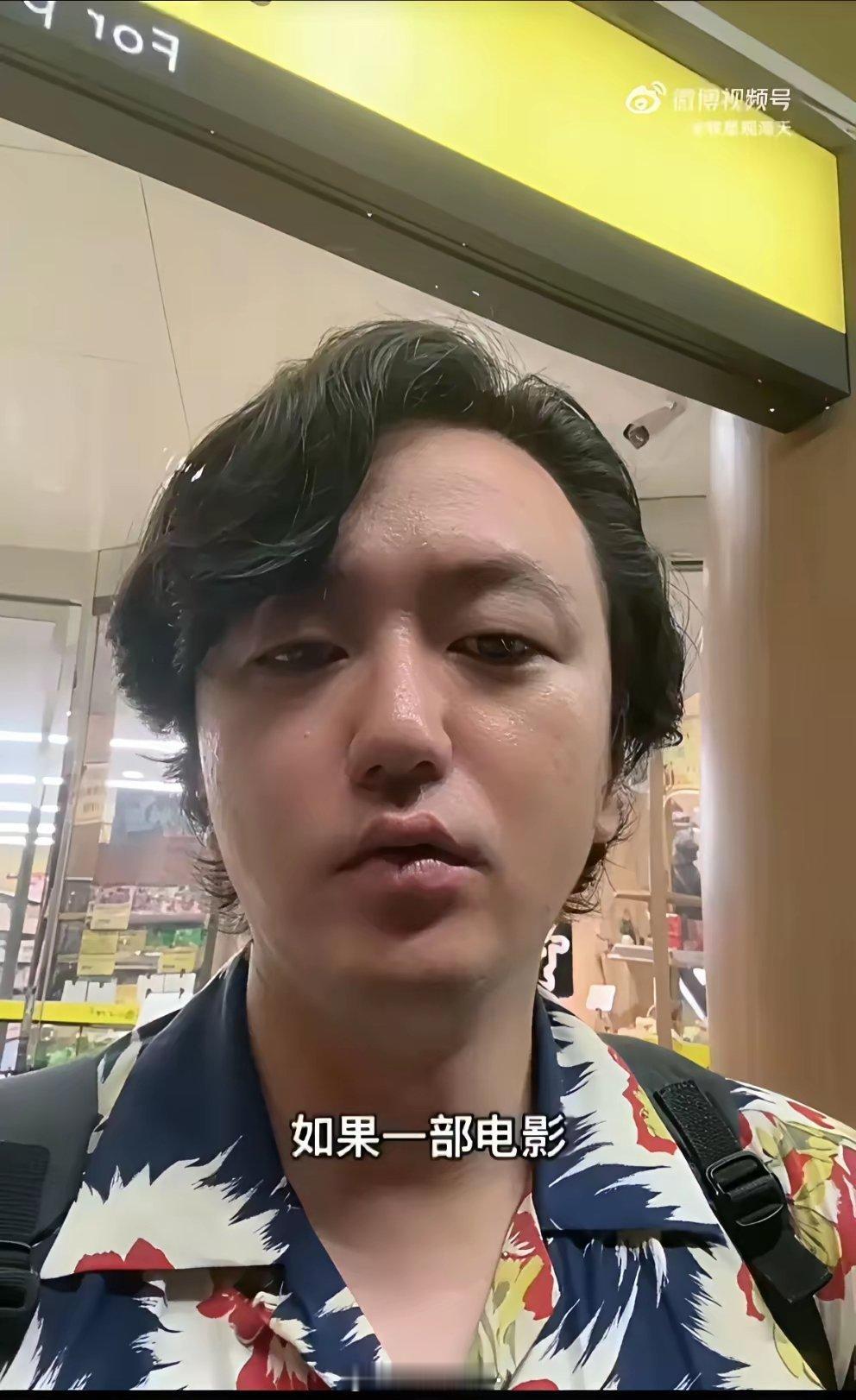1949年,沈醉接到去卢汉公馆开会的通知时,总觉得那些不对劲,可一时间又找不出破绽,等到发现问题时已经晚了!
沈醉,1914年出生在湖南湘潭,家里穷,母亲拉扯他长大。18岁通过姐夫余乐醒引荐,加入复兴社特务处,从此踏上特务之路。他身形瘦削,眼神犀利,办事谨慎,很快在特务圈子里混出名堂。抗战期间,他在上海干了不少暗杀和抓捕任务,手上血债累累,成了戴笠的心腹。抗战后,他被调到云南,当上军统云南站站长,专门盯着地方势力,搜集情报。1949年,解放军势如破竹,沈醉忙得焦头烂额,天天跑据点、见高层,试图稳住阵脚。 卢汉,1896年出生在云南昭通,彝族出身,年轻时进云南讲武堂,毕业后跟着龙云混,慢慢把滇军抓在手里。他身材高大,气场足,在云南军民中威信高。表面上他听国民党指挥,实际上早就跟中共暗中联系,盘算着起义。张群,国民党老牌人物,1949年当西南军政长官,穿着西装,斯文模样,但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。这三个人,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,在昆明这块风水宝地上演了一场大戏。
1949年12月9日下午,昆明街头冷风嗖嗖,军统云南站的办公室里堆满了文件,烟灰缸里烟头满得快溢出来。卢汉公馆的副官突然闯进来,递上一封信,说张群长官晚上10点在公馆开机要会议,沈醉必须到场。信上盖着张群的图章,字迹工整,就是内容少得可怜,没提开会干啥。副手徐远举接过信,瞅了一眼,确认图章没问题,催沈醉赶紧准备,说这种会不去可不行。沈醉却没吭声,盯着信封,手指摩挲着纸边,总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头。 他站起身,走到窗边,外面街头行人稀稀拉拉,空气里透着股不安的味道。他抓起电话,打到卢汉公馆,想找张群问清楚。接电话的人说张群不在,有啥事晚上开会再说。他又打到军统在公馆附近的秘密据点,问有没有啥异常情况,回答是啥也没发现。他不死心,又给几个友邻部门打电话,得到的回复都差不多:收到了通知,但没人知道会议内容。沈醉挂了电话,点根烟,烟雾在屋里飘散,他来回踱步,脑子里乱成一团。
沈醉多疑的性子让他没法安心,他总觉得这事有猫腻,但又找不出问题在哪。他决定多做点准备,召集站里的骨干开紧急会。会议室里烟雾弥漫,他站在桌前,布置任务:如果他晚上11点没回来,也没消息,副站长胥光辅得马上带人把重要文件和电台转移到26军军部,随机应变。他把钱包、证件、钥匙一股脑交给胥光辅,只留了几根金条防身。他还把新车钥匙塞给胥光辅,说这车跑得快,关键时候能派上用场。自己则挑了辆旧吉普车,发动车子,朝卢汉公馆开去。 路上,昆明夜色浓重,街灯昏黄,雨点打在车窗上,模糊了视线。沈醉开得不快,眼睛扫视着路边,留意每个细节。他路过军统的暗哨,哨兵站得笔直,没啥异常。到了卢汉公馆附近,高墙铁门在夜色里显得冷冰冰,门口卫兵背着枪,站得像木头人。沈醉把车开进院子,熄火后没急着下去,手还攥着方向盘,目光在院子里转了一圈。突然,他瞥见暗道里站着两个卫兵,枪口闪着光。他刚想踩油门走人,身后大门已经咔嚓一声关上。
沈醉硬着头皮走进公馆客厅,灯光暗得像蒙了层灰。张群坐在沙发上,低着头,双手搁在膝盖上,旁边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。沈醉一进来,张群抬头看了他一眼,摊开手,脸上挤出个苦笑。客厅角落的电话机孤零零摆着,电话线却被拔了。沈醉站在门口,扫视房间,空气死沉沉的。他瞬间明白,这场“会议”就是个套,卢汉已经把他们卖了。 这场所谓的机要会议,其实是卢汉精心布下的局。1949年,国共内战大局已定,解放军兵临城下,云南成了国民党最后的落脚点之一。卢汉作为滇军头子,早就看清风向,跟中共秘密接触,打算起义。他知道沈醉是军统的硬骨头,手上握着不少情报,直接抓人风险太大。于是,他借张群的名头,伪造了一封通知,引沈醉上钩。沈醉虽然多疑,但面对张群的图章和副官的说辞,加上连番查证没找到破绽,只能硬着头皮赴会。
卢汉这一招,堪称釜底抽薪。沈醉和张群,都是国民党在云南的关键人物,一个管情报,一个管军政,抓了他们,等于断了国民党在云南的臂膀。沈醉的谨慎帮不了他,军统的秘密据点也好,电话打探也罢,都没发现卢汉的计划。解放军在昆明周边已经布好网,卢汉的起义准备滴水不漏。沈醉一步步走进公馆,其实已经走进了解放军的包围圈。 12月9日晚上,卢汉正式通电全国,宣布云南起义,昆明迅速被解放军接管。沈醉和张群被押上一辆军车,送往临时拘留点。沈醉坐在车里,手被铐住,车窗外昆明街头一片寂静。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,他开始接受改造,整理文件,写下供词,交代军统在云南的活动。 卢汉因为起义有功,被任命为云南军政委员会主席,忙着处理地方事务。张群被押到北京,后来得到宽大处理,去了台湾,晚年低调生活。沈醉1960年获特赦,定居北京,写回忆录记录自己的经历,1981年因病去世。